马上注册,结交更多好友,享用更多功能,让你轻松玩转社区。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帐号?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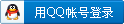
x
$ Y" a4 [/ w$ v$ y% E9 |
娘的农家小院 / S4 A! {, ^6 r! e$ y7 |3 `5 I
文/微澜 农家小院子里的丝瓜、豆角脆生生,緑得心醉,矮矮的压水井,静静地候着,一个蛮精神的老太太在忙碌。 那是丈夫的老家,有娘在,真正的家。娘勤劳,爱干净,也爱美,小院里种了丝瓜、梅豆,还有花草。它不像城里的公园,追求造型,也不像规模种植的菜园,整齐划一,而是随意种植,高高低低,角角落落,错落无序,颇有一种清秀婉约之气。 有古诗云:“寂寥篱户入泉声,不见山容亦自清,数日雨晴秋草长,丝瓜沿上瓦墙生。”丝瓜,在诗人的灵感里,是诗,在画家的上宣纸,是画,钻进摄影师的镜头里,是照片,在农家老娘眼里,那是能吃的菜。 小院里的丝瓜,没有专门的架子让它攀爬,只见它伸着长长的卷须探望着,树枝、矮墙、绳子,都是它的对象,微风一推,就像热恋中的女孩牵住了男朋友的手,或像调皮小娃娃勾住了爸爸的脖子打提溜。一天晚上,孙子的自行车停在旁边, 早上一看,它竟然抓住了车轱辘……没过不久,鲜绿的叶子旁边开出一朵朵金灿灿的小花,挂上一根根翠绿的嫩丝瓜。这时,娘伸手拽两个,就是一顿菜,清香嫩滑。 娘说:“长得最大,最好的,可不许拽,我要留种子。”到了冬天,丝瓜叶黄了,秧子干了,露出了几个黄棒子似的老丝瓜,拽下来挂在房檐下继续风干。娘闲了,把干透了丝瓜,剥掉外皮,拿着丝瓜瓤在石头上摔打,能甩出一大把黑色的圆圆的扁扁的耔儿,娘用小布袋装好挂在墙上,留到来年的清明前后种瓜点豆。干丝瓜瓤洗碗、刷锅、送人,听说还是一种药材,用处还真不少呢。 梅豆,也是攀爬植物,在柴堆上,在水井旁,自由攀爬,开白花,开紫花,像一只只花蝴蝶落在心形的绿叶上,长出的豆荚像一把把小弯刀,有紫色,有绿色,天越冷,秧长得越旺,荚结得越多……结多了,一下子吃不完,咋办?娘有办法。摘上一盆,抽筋煮熟晾晒。下雨了,娘用细绳把豆角围在蜂窝炉的圆圈,像戴了一串串“翡翠项链”,煞是好看。冬天,娘把梅豆荚泡软切丝,做面条,炒鸡蛋,还不失梅豆的原味。 不知是,梅豆不安分?还是丝瓜多情?他们会不自主爬到一起,也许是,风在做媒,也许是,离得太近,彼此熟悉了,相互凑在一起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娘嘴里念叨着:“各有各的地儿,别参搅。”其实,就像人一样,进了自家们,就是一家人,分什么你我。 压水井,是家里的功臣。最早,父亲在外工作,母亲带着年幼的孩子在家劳动,吃水要到外村的井台挑水,半大小脚的母亲,板着高高的挑杆很吃力,人多时还要排队,天旱时,还要起五更抢水……孩子稍大一些,两个人抬一桶水,再大点,会挑半桶水了,能挑满桶水了,娘笑了,不再为吃水发愁。 后来,闺女出嫁,儿子参军,娘也老了,农村也兴起了压水井。父亲心疼娘。请人在自家院里打了一孔井。自从有了压水井,娘整天都乐呵呵的,做饭、洗衣、浇园都离不开压水井。在井筒里倒上半碗水,一抬一落“咣当,咣当”几下,一桶水就满了。 蓦然想起,我们刚结婚时,第一次回婆婆家。那时,地处黄泛区的豫东北的乡村,土地盐碱,水咸涩苦很难喝。吃饭时,公公怕我吃不惯家里的饭,抓一把白糖放我碗里。后来我们带着俩孩子回去,爷爷对孙子也是这样往碗里放糖。 再后来,黄河不再泛滥,土地不再盐碱,家乡变成了粮食高产区。家家都有了压水井,有的家还安装了电机自动抽水,井水清澈甘甜,随用随压,吃饭再也不用放糖了,但老人的爱,家乡的情,还一直放在我们的心底。 丝瓜、梅豆、压水井,温馨着农家小院,丰富着老娘的生活,期盼着儿孙的归来。 房前的枣树,墙角的洋槐树,待到月升中天,清光从树间挥洒而下,地上疏影斑斑,尤为幽静,归来的儿女,轻声细语,聊东聊西,直到夜阑深深,归房就寝,月光仍然跟进窗里,助我们安然入眠。
" `1 P& z. z {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