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上注册,结交更多好友,享用更多功能,让你轻松玩转社区。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帐号?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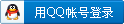
x
柿树长在心深处 静言 窰垴上长着一排柿树,七棵。每一棵都有三四把粗,棵棵都枝繁叶茂,葳蕤旺盛,张扬着勃勃生机。 柿树是爷爷种的,父亲十来岁就开始接管它们。浇水,施肥,打理枝干,采摘果实。 丘陵地缺水,每逢下雨,父亲戴着草帽,披着蓑衣,拿着铁锨、锄头,挽起裤管,光着脚板,在雨里挖沟、开道把水引进柿树坑,一淋就是大半天,汗水和着雨水在手下流淌,跌倒在泥水里是常有的。冬季,下雪了。父亲一锨一锨把雪端到柿树跟前,围着柿树堆成一座小山,柿树是雪山上的旗杆。春风化暖,大地上的薄雪融化了,那七座小雪山还能坚持好久。浇了水,还要施肥,记得父亲施肥的情景:在距离树根二尺左右的地方挖一圈大小适中的沟,把事先发酵过的牲畜粪、腐叶肥填在沟里,盖上一层薄土,然后浇上水,等水彻底渗下去,再填土封好。 柿树们在父亲辛勤照料下,茁壮成长,它丰富着我们的生活,伴随着我们长大。 柿树叶子肥厚硕大有质感,一片片挺挺地展着,像一只只手掌。它的正面油绿光滑,闪闪发光;背面呈灰绿色,涩而无光。每年夏天,我母亲做面酱的时候,都要摘下一些柿叶,清洗干净,铺垫在盆底、盆帮,待酱料装满,上面再盖上几层柿叶,然后放在阳光下曝嗮。柿叶既干净又清香,面酱吸收了它的精华,独具柿香,也把我们清淡而简单的生活调出了咸香味儿。秋天,柿叶由绿变黄,由黄变红,颜色十分瑰丽,像一幅浓笔油彩画。霜寒到来,柿叶悠然飘落。每天清晨,父亲把带潮的黄叶拢起,一筐一筐背回家。它是做饭、烙饼的好燃料,燃起了浓浓的人间烟火气。 柿花,很别致。色娇嫩,形特别,色是娇嫩的米黄色,形是方形外翻卷的小喇叭。我小时候,柿花是我的饰品,也是我的奢侈。母亲用柔韧的麦草杆,把柿花穿成项链、手链、脚链,挂在我的脖子上、手腕上、脚脖上。我成了最富有、最漂亮的小公主。睡梦里都在微笑。我常想,若那时留下影像,我会把它带到生命的终点。 采摘柿子是既累人又细致的活儿。低处的伸手可摘,高处的就要上到树上,并借助工具。父亲用一根细长木棍,顶端固定一个铁钩子,举起木棍钩子挂住柿梗,轻轻一拧,柿子带着小枝叶一起落下。树下我和姐姐扯着包袱四个角,仰着脸,紧盯着,稳妥地接住。收柿子也是最热闹的时候,全家人齐上阵,有的摘,有的接,有的拣,有的运。一家人忙并高兴着,柿子丰收了,一年的零食就有了,还可以换回些许零钱。 七棵柿树有四个品种:圆公公、鳖盖、火罐、小柿子。根据不同品种,母亲把它们制作成不同的柿子食品:圆公公个儿大脆甜,既可做漤柿,亦可做柿饼,漤柿大多拿去卖了,虽很便宜,也能换得半年的油盐钱。鳖盖柿子扁平皮薄多用来做葒柿,亦可做漤柿;葒柿能存放整个冬天,涂抹在粗粮饼上,那饼就香甜细腻了许多。火罐柿子圆而长刚好用来制做柿饼;小柿子则一切四瓣晾晒成柿瓣儿。小柿子还可以用来泡醋,酸而甘醇。柿子食品在我们这个多子女家庭起了重要作用。饿了,吃个柿饼或两块柿瓣,垫一垫,饿就过去了;遇到灾荒,它就是救命粮。母亲把干柿皮儿参上细糠磨成面,做成窝头,填充肠肚,孩子们得以安全度过荒年。平素常,它还是招待邻居的好果品,婶子、大娘来了,母亲端出柿饼、柿瓣儿,人们边吃边聊,其乐融融,乡情甜甜。 采摘柿子,父亲始终坚持:树上定要留下一些。留给,过路的,放羊的,飞鸟和玩童。父亲说:路旁之物,众者也。无论谁走到树下,喜欢了,就上去摘几个。即是收获到家的柿子,父母亲也总是这家一篮,那家一筐,分享给乡亲们。乡亲们世代相处,亲如家人,这种分享也是常事。 《酉阳杂俎》云:“柿有七绝:一多寿,二多阴,三无鸟巢,四无虫蠹,五霜叶可玩,六佳实可啖,七落叶肥大,可以临书。” 柿树,可谓树中君子者也。 我家的柿树,是一道风景,也是标识。秋天,柿叶翻红,丹果似火,远望,好似一条蜿蜒起伏的火烧云带,燃烧在窰畔;冬季,叶子落尽,铁色枝干上悬挂着火红的累累硕果。在清冷澄澈的天宇下,它们 “晓连星影出,暮带日光悬” 象一盏盏高高悬挂的红灯笼。 每次回家,看到它们,一股暖流就在胸中激荡;每当想家的时候,它们就亮在眼前,那是心中永不熄灭的光亮。 7 C4 w/ ?9 `' ^, o: n
|